-
亚历山大·潘佐夫:对杨奎松教授关于《毛泽东传》书评的回应
关键字: 《毛泽东传》潘佐夫杨奎松斯大林共产国际洛川会议洛甫张国焘季米特洛夫我认为这些毫无依据的指责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首先,杨教授除了毛泽东年谱外,没有征询其他的来源。包括,例如施拉姆(Stuart R. Schram)所著《毛泽东权力之路》(Mao's Road to Power)的“导言”一直到第5卷,刘英的回忆录,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第二,因为他没有认真读我的书,所以他没有意识到我写了不止他所谓的两个会议,而是写了三个,分别在7月18日、7月21日至22日(我的中文翻译误译为7月20日),还有8月4日至6日(可能杨教授不是很熟悉1935年8月4日至6日在沙窝举行的会议,也可能他把第二次会议和第三次会议搞混了)。第三,他没有仔细地阅读过《毛泽东年谱》第1卷,否则,他肯定会注意到逄先知等人确实写了毛泽东对于张国焘“严重错误”的批评。洛甫也这样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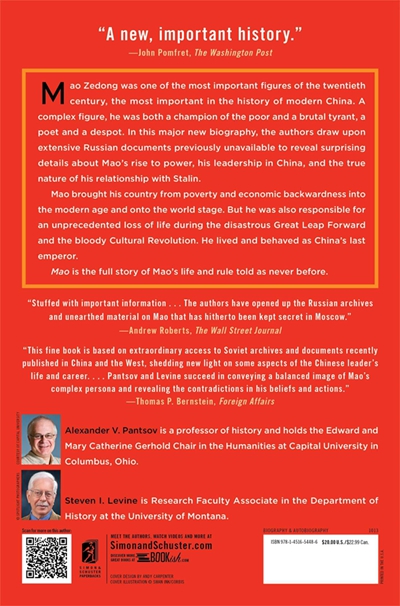
潘佐夫和梁思文合著的《毛泽东传》封皮
十二、 关于西安事变
首先,杨教授提到:“作者错把12月13日苏联副外长斯托马尼亚科夫对季米特洛夫说的话,当成了季米特洛夫自己的话。”(第22页)
很显然,这是由于俄语原文与中文翻译之间的不协调而产生的误解。相关研究者们都在使用俄罗斯和保加利亚档案馆所藏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时写的俄语日记原文,所以如果杨教授想要知道季米特洛夫对西安事变的真实态度,杨教授还需要研究俄文的原版材料才行。同时,在杨教授所引用的马细谱教授翻译的《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有一些杨教授可能未曾查证过的错误。
杨教授说,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13日在《日记》中写道:“斯托马尼亚科夫来见。他对张学良做出好的乐观的评价。苏联应该谨慎和巧妙地对待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反苏运动。”这与俄文原文完全不相符合。事实上,季米特洛夫于1936年12月13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关于张学良的部队在陕西起义的报道。逮捕了蒋介石。斯托马尼亚科夫在我的地方。乐观、赞赏地看待张学良。苏联需要克制、灵巧地应对与西安事变相关的反苏运动。”
季米特洛夫在日记原文中并未写道:“斯托马尼亚科夫”或者“他”“对张学良做出好的乐观的评价”。马细谱教授在翻译时错误地附带了“他”这个多余的字眼。《季米特洛夫日记》的原文清清楚楚地写道,季米特洛夫本人是极为高兴的。季米特洛夫当时是共产国际总书记,而斯托马尼亚科夫当时是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季米特洛夫的职务比斯托马尼亚科夫的职务要高,所以斯托马尼亚科夫不可能就苏联对西安事变需要怎么办的问题来教导季米特洛夫。斯托马尼亚科夫只是把西安事变报告给了季米特洛夫,然后季米特洛夫对西安事变表达了他个人的看法。只能说这是他们两人(季米特洛夫和斯托马尼亚科夫)对于西安事变的一致看法。
在1935—1936年,苏联外交部和斯托马尼亚科夫跟季米特洛夫一样,都遵循斯大林的政策。西安事变以前,斯托马尼亚科夫也经常致电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写道:我们要同蒋介石合作。但是,斯托马尼亚科夫和季米特洛夫都知道,斯大林不相信并且恨蒋介石。在此情况下,杨教授为什么以为,在听到西安事变消息后,斯托马尼亚科夫能对张学良做出好的、乐观的评价,而季米特洛夫不能对张学良做出好的、乐观的评价?我认为,他们两位都能做出好的、乐观的评价,因为他们都恨蒋介石,但是《季米特洛夫日记》明确显示:这是季米特洛夫做出好的、乐观的评价。所以斯大林给季米特洛夫打电话批评他。也许,斯托马尼亚科夫自己通知了斯大林,说季米特洛夫很高兴。
第二,杨教授提到我没有承认共产国际执委会(季米特洛夫)在听取和讨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邓发12月13日的报告之后,制定了一份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令草案。
这个指责很奇怪,因为《季米特洛夫日记》清清楚楚地表明,在12月13日,季米特洛夫没有听取任何邓发的报告。众所周知,邓发在西安事变发生前6个月左右来到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12月14日记录了,邓发的“信息变得相当的过时”。12月14日,在季米特洛夫了解了斯大林关于逮捕蒋介石的立场后,把邓发的过时报告简要地发给了斯大林,从而保护自己,同时把西安事变的所有责任推到了中共的身上。他写信给斯大林说,邓发的过时报告“显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不顾我们的警告和张学良建立了非常密切和友好的关系”;还说“很难想象张学良能不和中共商量协调就孤身犯险”。
第三,杨教授提到,在我的中文版著作中我错误地声称,在12月15日的清晨,“斯大林又给莫洛托夫打了电话,通知莫洛托夫第二天下午到斯大林同志办公室来,讨论中国事情。并要求莫洛托夫只和苏共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曼努伊尔斯两个人去”。他说,实际情况是莫洛托夫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第21—22页)这个指责也是不正确的,我没有写过斯大林打电话通知莫洛托夫。这是中文版翻译上的错误。在2016年9月12日他们写信给我,承认是他们的错误。
实际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没有给我充分的时间阅读全部的中文翻译校对稿就出版了这本书。2015年8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把中文校对稿寄给我,同时告诉我,出版社8月14日要出版我的书。所以,我只有一个星期阅读校对稿。我应该首先检查我书中“最敏感的部分”。在中文版中,我发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做了很多违反我和出版社之间协定的剪辑和改动,我不能接受这些剪辑和改动,因为它们涉及并改变了我对毛泽东的批评性意见。我应该同编辑商量,改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所做的剪辑和改动。总之,我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检查翻译的质量。
由此,我无法承担任何由翻译的错误而产生的责任。杨教授声称,他比了我的各个版本的《毛泽东传》(除德文版之外),为什么他在这里没有对照我的书的其他版本?
十三、 关于毛泽东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杨教授试图否定我的一段陈述:
毛需要汇报执行共产国际(12月16日的)指示(他实际于12月20日收到)的情况,但他同时也不想在自己的党内同志面前显得太窝囊。因此,尽管毛已经接受了莫斯科的指示,客观情况也有利,他还是没有与蒋介石签订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议。
杨教授写道:在1936年12月,“党的总书记不是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并不由毛负责。”他继续写道:“毛虽分工负责统战和军事,但在应对西安事变如此重大事件的基本决策问题上,当时也还是集体讨论决定……即使出了什么问题,首要负责者,也是负总责的总书记,而非毛。”(第22页)
在那时毛泽东不是总书记,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杨教授像是忘记了,毛泽东那时已经是最权威的中共领导人了,而且尽管他和总书记洛甫(张闻天)及其他领导人商讨,但所有最重要的决策几乎都由他制定。这就是为什么1936年12月17日和18日周恩来在西安发送他的与会报告时是发送给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而不是洛甫和中央委员会。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给了周恩来指示。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威也得到了莫斯科的承认。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不是对洛甫。在共产国际第七届代表大会上,宣布了毛泽东而不是洛甫,像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一样,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标杆”。
早在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他呈交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报告中就强调,遵义会议的结果是“我们驳回了‘铅笔战略家’,并推选毛泽东同志作为领导人”。与此同时,他对193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选择洛甫而不是博古担任总书记这件事只字未提。因此,斯大林只能考虑毛泽东而不是那个曾经在莫斯科学习的学生洛甫,作为他的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伙伴。顺便补充一句,不要忘记,在埃德加·斯诺1936年所写的书中,也称毛泽东为中共领导人,并且用一整章的文字来讲述毛泽东的人生故事,而提到洛甫的只有6次。这一章被立刻翻译并在苏联出版。苏联的新闻界是否也同样关注洛甫?不是。当然,毛泽东并没有把所有的电报都由自己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但是在1936年至1937年间他已经是实际的主要的决策者,而这些电报则传达了他的观点。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权威在中国也得到了承认。这是为什么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把逮捕了蒋介石的电报发给了毛和周恩来,而不是洛甫;这也是为什么斯诺的书中有关毛泽东生活的章节也在中国被立刻翻译并出版的原因。
杨教授同时讽刺地问:“要和蒋谈协议,也是远在西安的周恩来等才能谈,毛如何‘与蒋介石签订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议’?”(第22—23页)
首先,我并没有写过“签订协议”,而是“went slowly on concluding an agreement”。中文版本的翻译者还犯了一个错误,应该是“慢慢地达成协议”或者“慢慢地缔结协议”,而他们却写成了“签订协议”。但是我的书的翻译错误和杨教授的错误相比,我认为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在于,当时我写道,“毛泽东在与蒋介石慢慢地达成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议”,这并不是指毛泽东在协议签名时走得很慢。按照同样的逻辑,如果我们说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与希特勒达成协议,我们并不能假设这两人在文件上签署他们各自的名字,所有人都知道签署这份文件的是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如果我们说莫斯科和北京达成协议,我们也并不能假设莫斯科和北京所有公民都签署了这份文件。
十四、 关于洛川会议
杨教授声称,我在写关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的著名的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时,犯了几个错误。他说我错在:
洛甫起草并由会议通过的一个决议声称,为了赢得南京政府的“信任”和公共舆论的好评,八路军在最初阶段应该在与其他中国军队合作的情况下进行运动的游击战。该决议要求,在日军战线出现缺口的情况下,共产党控制的部队应转而进行独立的和纯粹的游击战,借此来扩大他们在日军华北占领区内军事行动的范围。
他说,我所用的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相关内容中“并无所引文字”。此外,他声称洛甫的决议根本不涉及军事问题。(第23页)

潘佐夫参加国内某学术会议(@BBC)
首先,他从我的书中引用的文字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的直接引用。我只是简单地转述了家喻户晓的故事。第二,洛甫的决议清楚地强调:“我们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本党所提出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而坚决奋斗。”而“十大纲领”等直接要求中共与中国的其他组织各自发展独立的游击战争。这两个文件在这方面是有交集的。
杨教授同时还认为,在1937年8月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可能谈论“扩大他们在日军华北占领区内军事行动的范围”。他写道:“华北敌后根本就不存在。”(第23页)
这是真的吗?我建议杨教授阅读有关洛川会议的文件和文献。所有的资料都会表明,毛泽东、洛甫和很多其他中共领导人,在会议之前和会议当中都谈到日军后方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抗日战争会是一场持久战。
此外,杨教授还声称,我扭曲了毛泽东在1937年9月1日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他事实上说毛泽东不可能在积极分子会议上讨论他的计划(即“要么我们战胜他们,要么他们战胜我们”),因为“毛泽东……只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小范围会上去争论”。(第23—24页)
我很遗憾不得不再次推翻杨教授的结论,因为毛泽东确实在积极分子会议上透露了他的计划。至少有作为即将召开的会议的发言稿为证,他写道“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我可以同意他的措辞和我的中文版本译文略有不同,这主要是因为我的中文翻译可以轻易地直接地从原始文本中摘抄毛的话,而不像我的书的俄文翻译。然而,从根本上说,意思是一样的。
十五、 关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在杨教授的书评中题为“‘新民主主义’是斯大林的阴谋?”的一节中,杨教授显然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说法。在第8页,他声称就“新民主主义论……受到过莫斯科的直接影响”这个观点他曾“做过较深入的研究”。然后,他试图谴责我,因为我认为毛泽东的概念源自于克里姆林宫的“老板”斯大林于1937年11月11日发给中共领导人的战术指令。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杨教授承认,在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确实向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以及康生发出了以下指示:
- 原标题:亚历山大·潘佐夫 | 对杨奎松教授关于《毛泽东传》书评的回应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武守哲
-
● 观察者头条 ●风闻 · 24小时最热 查看全部>>最新视频最新闻 Hot
-

请吸毒艺人站台遭抵制,NARS发声明又被批
-

又一家要“倒戈”,这次是美国最大铁钉制造商
-

哈雷“叛逃”后 特朗普破例为郭台铭站台:将出席富士康在美动土典礼
-

梦想成为中国公民的美国人:我发现中国人更善良
-

全美国都在问:她是谁?
-

这国上演近代史上最血腥大选 100多名政客被杀
-

白宫发言人被赶出餐厅后,一万多人怒了…
-

“黑公关”大战中,腾讯推新游戏“逼”你学微积分
-

美国要求所有国家11月停止进口伊朗石油 否则制裁
-

美媒:中国没必要“恢复”任何王朝,现代化也不等同西化
-

特朗普真的怒了:海外建厂将是哈雷的“末日”!
-

英国人请愿:让“特朗普宝宝”飞
-

哈雷生产线要移出本土 特朗普惊了:投降派
-

澳智库称华为是澳高官海外出行最大赞助商,外长在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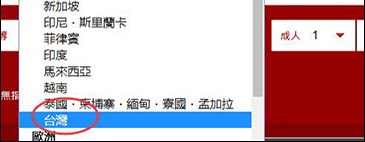
日本两大航空改标还玩起“小伎俩”
-

日媒找到世界杯对手“强壮的秘诀” 中国网友都说眼熟!
快讯 -
Copyright ? 2018 观察者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备10213822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220170001 违法及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21-62376571
![]() 沪公网安备 31010502000027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502000027号
![]() 中国互联网举报中心
中国互联网举报中心
 上海市互联网违法与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上海市互联网违法与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